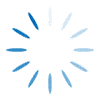ps:一下为出版精修版,和原文剧情一样,看过的书友不必再订阅!
===================================
我是一个靠死人养大的人。
我家在川西山区,父亲是当地的八大金刚。
别听这名字威风,事实上有点年纪的都知道,这八大金刚是什么意思,川西山区重丧葬,人死了得有八个人抬棺材,俗称八大金刚。
我父亲总是站在右边第三排,按照风俗这个位置叫五鬼抬棺,意思是说死的人德高望重,连鬼都要来帮忙抬棺,因此我父亲被称为顾五。
当八大金刚有很多好处,每人一整包香烟,发丧前的饭桌上有两大碗红烧肉,比其他桌多了一碗,八人围坐一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关注下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吃饱喝足孝子还要送上八个红包。
可山里人多忌讳,认为八大金刚中五鬼抬棺这个位置不吉利,不但会死于非命还会祸及后代,因此即便是再穷的人也不愿意干这事,当时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所以但凡有丧葬他必定是雷打不动的五鬼抬棺人。
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母亲,所以父亲外出只有带上我,五鬼抬棺人的名声在当时的川西山里很大,但凡死人总会请我父亲过去,好在那年头隔三差五的都有人死,因此我几乎是靠吃死人丧宴长大的。
下葬的时候父亲有一个习惯,总是会在坟地最下面取一把土在手里搓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父亲这个动作的含义,偶尔空闲在家父亲就会翻来覆去看一本书,我最先能认的字便是那本书的书名。
入地眼。
后来才知道这书是一本北宋葬书,传写数百年,秘之已久,被堪舆家视如珍宝的阴宅风水全书,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只要按照风水堪舆下葬,熟读此书都能找到陵墓的所在。
父亲唯一的爱好便是看书,再大一点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父亲收藏的书,不明白一个山里给死人抬棺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书。
在父亲身边时间长了耳闻目染,对那本入地眼全书也能知晓一二,最让我奇怪的是这些书里,还有一本是记载江湖切口的,也就是所谓的黑话,我一直不明白父亲看这些的原因。
日子虽然平淡清贫但却安稳,我本以为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一天黄昏父亲跌跌撞撞从外面冲进来浑身是血。
他紧紧抓住我把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条石头吊坠项链戴在我脖子上,叮嘱无论如何也不能遗失这条项链。
并从房梁的罐子中取出一个用油纸包裹的东西交给我,让我立刻从屋后立刻有多远走多远再也不要回来,而且油纸里的东西务必要烧掉。
第一次看见父亲如此恐慌我茫然的不知所措,父亲吃力的冲着我大吼,我惧怕的抱紧父亲交给我的东西向后山跑,等我跑到山腰时候刚好能从草丛里看见我家。
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中山装的人,父亲被拖到外面殴打已经站立不起来,站在最后面的人走上去和我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摇头嘴都不张,最后那人站起身握拳竖起大拇指在脖子上划动一下。
站在两边的人突然向我父亲开枪,我在山腰草丛中捂着嘴恐慌的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杀的整个过程。
那些人杀掉我父亲后冲到房中到处翻找,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最后走的时候点燃了房屋把我父亲丢在里面,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应验了鬼抬棺的人会死于非命,而我也变成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孤儿。
我没有再回去一直沿着后山拼命的跑,去什么地方根本不知道,直到深夜我才停下来,我找来树枝生火坐在火边瑟瑟发抖害怕的不敢哭出声。
一直紧抱在怀中的油脂包掉落在地上,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到最后都如此紧张这东西,用颤抖的手打开发现里面包裹的是一本残缺的硬皮笔记。
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大部分我都认识可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语句也不通顺像是随手练字时写的,而且大多页面像是被烧毁过残缺不全。
但我很肯定是父亲的亲笔,因为父亲是左撇子他写的字习惯性向右倾斜,这笔记里记载的内容我完全看不懂,翻到最后一页有东西掉落出来。
我从地上拾起来,那是一张泛黄的残缺照片,其中一半被烧掉,剩下的一半中我惊诧的看见,穿着特殊军装面带微笑,意气风发的父亲,在他的前面和旁边也是露出笑容的军人,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防毒面具。
照片的背景很诡异,整个大地一片焦黑却闪耀着绿色的光芒。
我在照片右下角看见标注的日期,1965年5月14日,AM9:45。
而在日期的下面还有一组当时我看不懂的数字。
E41.43、N88.44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父亲留在笔记中,那些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可惜那本笔记在山林中被我按照父亲的话烧掉,这让我后来意识到时追悔莫及,笔记中那些我看不懂的文字,应该是经过加密书写的日记。
我没想到父亲竟然会是一名军人,直到后来我反复琢磨,照片中那一组奇特的数字,才发现那是一组经纬度坐标,在地图上对比后得到一个地名时,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会书写加密的日记。
罗布泊。
1964年红色王朝在罗布泊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核试验!
谁会想到一个给死人鬼抬棺的山里人,竟然参与了红色王朝在罗布泊的核爆实验,但很肯定我父亲当时参与了,甚至比核爆试验更为机密的事。
这还不是让我感觉最震惊的,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张照片真正诡异的地方。
我从一张陈旧的报纸上,一则大版面新闻里看见照片中的日期。
……1965年5月14日上午10点,红色王朝成功对西部地区北纬40°东经90°进行第二次空投核爆试验,据地面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时距靶心仅40米……
照片中父亲和那些军人所在的经纬度正好是靶区,他们照片拍摄的时间是上午9:45,而在15分钟后他们将遭遇一颗被空投到距离他们只有40米爆炸的原子弹。
没有人可以在核爆中心区域存活下来,巨大的核裂变威力能摧毁周围一切。
一直拉扯我长大的父亲应该在1965年5月14日和照片中其他军人死于核爆!
话又回到最开始。
我是一个被死人养大的人……
从山里逃出来是三个月以后,蓬头垢面浑身肮脏的像一个野人,两天没有吃过东西我实在饿的不行,最麻烦的是寒冬腊月,我身上早已破烂的衣服,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我瑟瑟发抖冻饥寒交迫,打算去地里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吃的,走了很久看见山坡上有冬梨树,刚打算爬上去就被人从后面一把拽到地上,一只粗糙的手紧紧按在我嘴上。
昏暗的月光下我看见一个凶神恶煞,脸上有一道伤疤的中年人,目光警觉的张望四周,任凭我怎么挣扎也动弹不得,片刻见没动静伤疤捂着我嘴把我拖到树林深处。
我这才看见树林里还有七八个穿着奇怪衣服的人,灰色的连体斗篷却没有袖子,完全和夜色融为一体,这些人如果不动我根本发现不了,他们手里各自拿着铁锹、锄头和竹筐,其中一个中年人坐在石头上看着手里的怀表,很淡定的向我瞟了一眼。
伤疤压低声音说:“掌柜,抓到芽子怕是钩子,晓不得棵子里面有没有伏着点儿。”
周围的七八个人一听,手里的家伙事全都扔掉,麻利的掏出明晃晃的刀,被称为掌柜的中年人收起怀表,依旧处变不惊的回了伤疤一句:“并肩子,念短,要是合字上的朋友,一碗水端来大家喝,是点子进来条子扫,片子咬。”
我被伤疤捂的喘不过气,听他们对话心里更是一惊,这些人说的都是黑话,好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看过一些,大致明白是什么意思,伤疤是说我是探子,担心外面草丛中还埋伏着其他人。
并肩子是兄弟的意思,念短就是别出声,那个被称为掌柜的回的是,让这七八个人警惕点,如果是道上的朋友合伙求财见者有份,如果是想黑吃黑放进来枪扎刀砍。
我一口咬在伤疤的手上,他吃疼,呲牙咧嘴不敢发声,一把将我丢在地上,本来就饿的没力气被摔在地上头昏眼花,估计当时也是吓傻了,吃力的爬起身一个劲的摇头。
“我不是探子,没有其他人,我来这里想找吃的。”
这话从我口里说出来那个叫掌柜的一愣,顿时警觉起来,对其他人使眼色,那七八个人和伤疤都小心翼翼潜入草丛中。
我看见掌柜手里也多了一把刀,样子有些紧张,过了许久其他人都回来,伤疤对他摇了摇头,掌柜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收起刀重新打量了我半天问。
“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
我这才意识到他为什么刚才会突然警觉,毕竟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也不该懂这些黑话,我点点头,掌柜又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目光落到我身上,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不敢说话,这些人看样子就知道不是善茬,伤疤见我半天不吭声,冲上来就是一脚把我踢倒在地,脖子上的项链被挂断掉落在掌柜的面前,伤疤在我身后压低声音骂:“这芽子不老实,能听懂我们说话也不是什么好鸟,装傻充愣就是欠收拾。”
伤疤一边骂一边又一脚踢在我身上,见我还是不吭声怒不可歇一把将我从地上拧起来,这三个月我学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活下去,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就在被提起来的同时重重砸在伤疤的头上,顿时他眼角裂开鲜血直流。
估计伤疤都没想到我居然会反抗,这一下砸的不轻我几乎是用尽全力,伤疤捂着眼角气急败坏,刚想冲过来我就听见身后掌柜的呵斥的声音:“够了,这么大的人怎么和一个细娃杠上。”
伤疤虽然咽不下这口气,可对掌柜的话却言听计从,看得出这些人里面掌柜是发号施令的,掌柜看向我,又重新问了一次,知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挖红薯的。”我紧握着石头脑子一热脱口而出。
掌柜又愣了一下,就连被我砸伤的伤疤和其他人也面面相觑的对视,好半天我看见掌柜脸上浮现出笑意,这挖红薯当然不是真来地里挖红薯,黑灯瞎火在荒郊野外说着黑话,不用想也能猜到这些人干的不是正当营生。
打家劫舍不会选这里动手,杀人越货也不会挑这地方,唯一能做的就是盗墓,而黑话中在山野田里盗墓被称为挖红薯。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挖红薯的?”掌柜也不否定若有所思的笑着问。
如果再大一点我绝对会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可那个时候我才十三岁,面对一群凶神恶煞不知来历的人,只想着说完他们会放我手,我抬手指着周围的树林回答。
这里四周都是树园,连绵在一起几十亩,明堂开阔,左边土丘绿荫成林如白虎伏降,后面倚靠三座大山,大峰刚直,二峰华峻,右边的河围绕明堂而过,犹如狮子扑兔,这样的风水绝佳乾坤拱照之地,埋在这儿的后人必定福音无穷。
在风水堪舆中这里被称为狮子下山,是上好的风水之地,而掌柜如今所坐的石头正是宝穴的位置,下面一定有墓,而且埋在下面的人非富即贵。
这些都是我从父亲那本入地眼中学到的,等我说完几乎所有人都一脸震惊的看着我,掌柜的嘴都微微张开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毕竟这些话从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任何听到的人都会吃惊,掌柜很好奇的问。
“谁教你的?”
“我爹。”
“你爹人呢?”
“死了……”我声音有些黯然。
“那你娘呢?”掌柜迟疑了一下声音有些缓和。
“没见过。”我的回答更加低沉。
掌柜半响没有说话,突然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吓了我一跳,这才知道那天是除夕夜,迎新的鞭炮让寂静的深夜变的嘈杂,掌柜对着旁边的七八个人点点头。
我看见他们猫在树林用力按下一个把手,沉闷的爆破声从地底传来,但完全淹没在爆竹声中,我这才明白掌柜一直看时间的用意,他是在等迎新的鞭炮声来掩饰盗墓的爆破声。
没过多久有人从树林中回来对掌柜点点头,看样子应该是得手,然后其他人开始准备绳索,掌柜从容的从怀里掏出一个酒壶和两个白面馍对其他人说:“别慌,时间还早,先等下面敞敞气。”
寒风中我看见他手中的白馍,一边冷的发抖一边忍不住吞咽口水,掌柜喝了一口酒看见我忽然笑了笑,把酒壶递给我:“喝一口就暖和了。”
我迟疑了一下抿着嘴怯生生走过去,接过酒壶想都没想大口喝下去,辛辣的酒烧呛得我不停咳嗽,那是很烈的酒对于从未喝过的我来说简直承受不住,烧的胃难受想吐可的确是暖和了不少。
旁边的人看着我嘲弄的大笑,当时不服气咬着牙再灌了两口,酒壶被掌柜夺过去,豪气干云的笑了笑:“这细娃还强横的很,将来也是难缠的主。”
几口烈酒下肚身子倒是暖和可头晕的不行,我从地上拾起刚才被扯断的项链,那吊坠上的石头不知道怎么竟然分开,掌柜的目光落在项链上,眉头一皱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的凝固在脸上,一把将项链拿过去。
“还给我!”我再一次握紧手中的石头,那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掌柜收起脸上的笑容一本正经的问。
“我爹给的。”我愤怒的盯着他回答。
“你爹叫什么?”掌柜并不在意我的反应,表情变的有些焦急。
“顾五。”
“顾五……?!”掌柜在嘴里反复念叨这个名字,样子有些茫然的疑惑,好半天才把项链还到我手上,可那吊坠上的石头又合拢,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系好后戴在脖子上。
我一直专注着掌柜手中的白馍,而他却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远处的爆炸声渐渐稀疏,他估计是看见我对着白馍不断蠕动的喉结,慢慢把白馍递到我面前,然后指着不远处刚才被炸开的洞意味深长的问。
“敢不敢下去?”
那盗洞不知道有多深,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可对于我来说面前这白馍的诱惑力完全比对那盗洞的恐惧要多,我想都没想一把接过掌柜手中的白馍狼吞虎咽吃下去,执拗的抹了一把嘴。
“敢!”
掌柜对其他人点点头,伤疤把绳子绑在我身上吊我下去,盗洞里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大概下到七八米才我脚才踩到底,打开伤疤交给我的手电我竟然踩在棺椁上。
手电的灯光穿过腐朽的棺椁,我正好看见里面的尸骸,骷髅头上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眶正阴森森盯着我。
手一抖手电掉落在地上,几米深的地底我一个十三的孩子,四周漆黑旁边还有一具剩下骨架的尸体,冷汗顿时吓了出来,摸索了半天才找到手电,就听见伤疤在上面没好气的骂声。
“你怕啥,没出息的玩意,死的只剩下几根骨头,又不会爬起来咬你两口,别像个娘们在下面磨唧,把能搬动的东西都装到袋里。”
灯光中我看见上面吊下一个麻袋,我在下面呸了伤疤一口。
“有本事你下来,谁怕谁是小妈养的。”
我还真不是怕,从小到大我见过的死人敢说比上面的人多,只是刚才突然看见多少有些没反应过来,伤疤怒不可歇在上面继续骂。
“王八犊子,嘴还硬实,看老子待会怎么收拾你。”
我没理会他把下面能拿走的东西全放在麻袋里,前前后后运了好几次,等到最后一麻袋被拉上去,我再没见到绳子放下来,寒冬腊月我本来就冷的不行,在地下更是冻的发抖。
突然心中一惊,父亲对于墓葬似乎格外有兴趣,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
盗墓是玩命的行当,不但要慧眼识宝,更重要的是慧眼识人,所谓华山险人心更险,下墓挖宝最怕的就是见财起意。
这群人半夜三更来这里还说着黑话摆明就是不想有人知道身份和行踪,何况我如今还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就是被这群人活埋在这里也没人知晓。
刚想到这里我抬头就看见伤疤走到盗洞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嘴角挤出一丝冷笑,从上面踢下一些土落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
“王八犊子,叫你嘴硬,既然你能听懂黑话,那你知不知道啥叫沉地仙?”伤疤在上面趾高气昂冷冷的问。
沉地仙是盗墓行当的切口,意思是活埋。
我朝旁边呸了一口,拾起地上的石头就向上面砸去,看架势这群人是铁了心要灭口,我说什么都没用,伤疤迎着光看不见我砸向他的石头,眼看就要打中伤疤从旁边伸出一只手稳稳接住,掌柜走到上面的盗洞边白了伤疤一眼。
“半天时间不到你就被一个细娃伤了两次,你还有脸在这儿耍嘴皮子功夫,赶紧带人收拾东西撤。”
我心里当时多少有些绝望,看着掌柜蹲在盗洞上面盯着我看了很久,若有所思的问我。
“真的不怕死?”
“男儿到死心如铁!”我挺起胸稚嫩而倔强的回答,这是父亲教我的,事实上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只感觉好像现在说出来挺合适。
掌柜在上面似笑非笑的摇头,扔下一个白馍,我也没想那么多,毕竟那个时候年纪小,对死亡还没有多少概念,横竖要死也得吃饱了再说,掌柜在上面好半天才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爷叫顾朝歌。”我一边狼吞虎咽吃着白馍一边傲气的回答。
掌柜在上面乐呵的笑出声,然后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消失在洞口,那一刻我所有的豪迈和倔强完全被恐惧和害怕淹没,咽下最后一口馍我发现自己浑身在发抖。
我突然听见上面又传来掌柜豪气干云的笑声:“顾朝歌……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是个好名字,能爬上来就跟我走。”
一根绳子从上面扔了下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处逢生,不过很多年后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事才意识到,或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注定从那根绳子爬出来的我将开启一段惊险、神秘而且匪夷所思离奇的传奇之旅。
我被掌柜带回成都,他在小关庙经营一家规模不小叫四方的当铺,80年代的时候小关庙在成都古玩界的地位相当于潘家园,因为每逢晚上12点才开市因此故名鬼市。
掌柜姓叶,叶九卿的名号在当时小关庙鬼市很吃的开,但从来没人直呼他的名字,总是客气的敬一句叶掌柜。
做古玩生意的来路无非两种,见的光的摆在摊位上卖,还有些见不得光的你敢卖不见的有人敢收,说白了都是从墓里摸出来来路不干净的,行当里称为老鼠货。
叶九卿聪明掉脑袋的事当然不会干,便有了这家叫四方的当铺,只典当不销赃,东西往柜台一放朝奉估价开单给钱,真要是追查下来充其量也是典当的东西怎么也和盗墓贼赃沾不上边。
后来我才搞清楚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这四方当铺其实也是一个幌子,暗地里干的就是盗墓的营生,西南地区把盗墓贼称为土耗子,四方当铺就是一个耗子窝,耗子头当然是叶九卿大小事情都由他决断。
下面是师爷封承负责收集消息和支锅的金主接洽,然后是专门负责挖墓腿子魏虎,也就是被我打伤的伤疤,四方当铺的人叫他将军,负责估价鉴定的叫赵阎。
我跟叶九卿到四方当铺的时候,他让将军把我像拧小鸡一样推到柴房,烧了两大锅热水像烫猪般把我洗干净,扔给我的衣服都大的像戏袍,当铺的人围过来哄堂大笑,我倔强的怒视所有人,换来的却是脸被这些人轮流捏了一遍,甚至还有弹我牛牛的……
叶九卿让人给我一碗饭上面还有肉,没吃完他就把一张纸摆在我面前,他说当铺有当铺的规矩,拿了当铺的钱得九出十三归,还不起就得有东西抵押,吃了当铺的饭也一样,我算是欠了当铺的得先签了当票。
当时我只顾着填饱肚子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稀里糊涂就被叶九卿抓着手印上红泥在那张当票上按了手印,完事他才告诉我,这当票算是断当,意思是说东西典当后在期限内没有赎回,这东西就算是当铺的。
一顿饭我就稀里糊涂把自己当给了叶九卿,而且还是断当,说简单点我这条命从按下那个手印开始都不算是我的。
我就是这样留在了四方当铺,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四方当铺里这帮人也没我想的那么坏,前面十三年我是靠父亲带着吃死人丧宴养活,后面的十年我就是被这帮发死人财的糟老爷们拉扯大,就如同我最开始说的那样,我是被死人养大的这句话一点不为过。
在四方当铺我最开始只是学徒,不过所有人都戏虐的叫我小爷,因为第一次见到叶九卿的时候我在盗洞里就是这样傲气的回答他,敢在叶九卿面前称爷的估计也就我一个人了,这事沦为四方当铺的笑柄时间长了所有人都这么叫我。
俗话说跟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扛邪神,一个小孩天天跟着一帮无法无天恶贯满盈的盗墓贼能学到什么好的。
叶九卿是探墓高手他一直逼着我学他的探墓手法和本事,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还是因为我从小看父亲那些书有底子。
十年时间我看着叶九卿慢慢发福长胖,等他走路腰上的肉都会抖时我已经学完他教我的一切,唯一没有的就是经验,因为叶九卿虽然教我探墓但从来不让我参与其中。
将军会带我去一些被盗过墓教我如何挖墓,从最开始怎么用洛阳铲甚至第一铲探洞都是他手把手教我,然后是打盗洞和如何下墓摸宝,他教了我十年也边打边骂了十年,从来没被他打服过倒是身子被他打的越来越瓷实。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三十五的汉子,十年后挖一个盗洞我能看见他有些力不从心的喘息,估计是真打不动我了,不过我也让他知道这十年没白教,没想到他会给叶九卿说青出于蓝这四个字。
除了被叶九卿和将军教我这些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封承呆在一起,他和我父亲挺像,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他也逼着我看同时也教我书里的东西,封承是很严谨的人话不多但都入木三分而且学富五车博古通今。
封承说我天资聪慧机智过人而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所以他教的东西,我总是能很快的烂熟于心并且融会贯通,都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二十三岁的时候小关庙鬼市都知道四方当铺有一个既能耍流氓而且还有文化的顾小爷。
在当铺当朝奉的是赵阎,六十多岁还是老不正经,当年弹我牛牛的就有他,他只要上到柜台就板着脸不苟言笑虽然带着老花镜那双眼睛盯着谁看都透着寒意,行当里叫他赵阎王。
倒不是他有多厉害,阎王判生死,他判的是真伪,送来典当的土货经过赵阎的手,真假贵贱半分钟不到就能断出来,赵阎就教我如何鉴定分辨古玩真伪。
他们足足逼我用了十年时间学会这些本事,可我对这行当完全没有丝毫兴趣,在他们的调教下我圆滑世故而且嚣张,几乎除了叶九卿外四方当铺每一个人都被我捉弄过,他们怕叶九卿至少他还讲道理,而我却是玩世不恭全凭喜好。
刚到四方当铺的时候我十三岁,十年以后他们就真把我当爷了,估计这帮养大我的糟老爷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年被他们掐脸弹牛牛的小孩会变成如今送都送不走的顾小爷。
但随着学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渐渐意识到小时候一些没有留意到的事。
我最开始见到叶九卿他们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着的那种带着斗篷却没有袖子的衣服叫老鼠衣,是土耗子夜间专门穿的衣服。
不但能掩饰行踪而且行动方便,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这衣服的名字但一眼就认出来,因为我父亲也有一件这样的老鼠衣。
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每次去给人抬棺下葬的时候,他总会从坟坑最下面抓一把土搓揉,现在细细回想才明白父亲当时是在判断这些土质的成分,那手法完全和叶九卿教我的探墓手法一样。
还有那本入地眼的风水堪舆古书,我在封承的书架中也有看到过,但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在封承那里看到的入地眼内容明显和我父亲的有出入,父亲那本记载的更加详实和精确,甚至很多篇幅封承收藏的入地眼中根本没有。
入地眼虽说是风水堪舆奇书,但任何事都有两面,精通入地眼可以找寻风水宝地为人定穴下葬,同时也可以根据入地眼上的记载找到陵墓的位置,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并且接受一个事实,我父亲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五鬼抬棺人,他暗地里更像是一个盗墓贼!
随着年龄的变大我发现那个我以为最亲近的父亲有太多的秘密我并不知晓,我甚至都没搞明白他的真实身份,直到我在地图上对比被我在山里烧掉硬皮笔记中的坐标,才得知父亲的诡异。
从那些断断续续并不完整的日记中,我能判断父亲是一个曾经参加过国家最高机密实验的军人,但父亲涉及的机密恐怕远不止这些。
我在脑海里经常会勾画出一个沉默寡言山里的五鬼抬棺人和一个背景神秘的军人以及一个不为人知的盗墓贼,这是目前为止我所知父亲的三种身份,可即便我绞尽脑汁也始终无法把这三个完全不相干的身份关联到一个人的身上。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